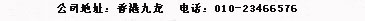治疗中风高血压癫痫乙脑支气管肺炎
导读:羚角钩藤饮,出自清·《通俗伤寒论》。具有凉肝熄风,增液舒筋之功效。主治热盛动风证。高热不退,烦闷躁扰,手足抽搐,发为痉厥,甚则神昏,舌绛而干,或舌焦起刺,脉弦而数;以及肝热风阳上逆,头晕胀痛,耳鸣心悸,面红如醉,或手足躁扰,甚则瘈疚,舌红,脉弦数。临床常用于治疗乙型脑炎、高热痉厥、原发性高血压、高血压脑病、产后惊风、妊娠子痫等属肝经热盛,热极动风,或阳亢风动者。
方歌羚角钩藤茯神地,芍茹川贝甘桑菊,肝热动风热不退,烦躁神昏手足搐
组成羚角片(先煎)一钱半,霜桑叶二钱,去心京川贝四钱,鲜生地黄五钱,双钩藤(后入)三钱,滁菊花三钱,茯神木三钱,生白芍三钱,生甘草八分,鲜刮淡竹茹(与羚角先煎代水)五钱。
用法用鲜淡竹茹与羚羊角先煎代水,煎上药服;现代用法:羚羊角一般宜锉末冲服,每次0.5一1g;或以大剂量20一30g的山羊角代用,水煎服。
功效凉肝熄风,增液舒筋
主治热盛动风证,症见高热不退,烦闷躁扰,手足抽搐,发为痉厥,甚则神昏,舌绛而干,或舌焦起刺,脉弦而数。以及肝热风阳上逆,头晕胀痛,耳鸣心悸,面红如醉,或手足躁扰,甚则瘈疭,舌红,脉弦数。
方解
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:“诸风掉眩,皆属于肝”、“风从内生”。
对内风来讲,理论性比较强,对内风的认识,中医学是经过了可以说不到两千年的时间,才把它搞得比较成熟。《内经》里面,外风和内风是不分的。都是风。遇到风就要散。到唐代时,仍然外风内风是不分的。到宋金元时期,很多人才提出来,这个风,对内风、外风提出了疑问,所以对风的证候,内风证候不把它和外风混淆,很多医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比如刘河间,刘完素,第一个他提出来,这种风,它是跟热有关。不仅仅是外来的风。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,他说这跟虚有关,风这类证候和虚有关。朱丹溪认为风、动风这类,肝风内动动风,当时还不叫肝风内动,他说不是外来风,这个跟痰有关。发展到张景岳时代,明代,《景岳全书》里就对内风提出来,跟气血痰三者有关,而且他明确的指出来,中风非风,就是说这种内风引起的中风,不是外来的风邪,中风非风,当然如果讲不是风,是什么呢?他讲跟气血痰有关。但整个病机能够很清晰的把它描述出来,应该说是叶天士,明末清初的叶天士,才提到阴虚阳亢。那肝肾阴虚,阴不制阳,阴虚要阳亢,阳亢肝阳化风。对中风病,这个内风的看法,历史上经过了,在实践当中,从疾病和疾病斗争过程当中,经过了一、二千年,才探索到把中风,内风、外风应当分开。
平熄内风,这个内风和外风,是要严格区分的。内风有几类
1.热极生风 ─ 我们最常见的,热极生风一般是在热病的极期,热病以发热为主,外感热病当中,发展到极期阶段,往往以高热为特点。可以高热灼伤津液,筋脉失养,造成动风。这种热极生风治疗药凉肝熄风,代表方像我们后面要讲的羚角钩藤汤。
2.肝阳化风 ─ 肝肾阴虚,阴不制阳,造成肝阳上亢,肝阳上亢引起了气血上逆,肝阳化风,那只有滋补肝肾之阴,平肝达到熄风的作用。所以叫平肝熄风。
3.阴虚风动 ─ 阴虚风动是温病的后期,这和羚角钩藤汤证的热极生风不同。一个是极期,一个是后期。热病的后期,这个时候,热病伤阴,人体的真阴亏损了,阴伤程度较重,那就是说筋脉失养的程度有很重了。这是以虚证为主的,我们叫阴虚风动,要滋阴熄风。这是以虚证为主的。
实际上这三类内风,热极生风证是以实证为主,肝阳化风证是以虚实夹杂,本虚表实证,阴虚风动证是虚证为主,三个基本类型。这是治疗内风前面的概述。
由于内风、外风的由来不同,所以在治法上也有严格的区分。外风宜散,内风宜熄,外风要用辛散之品,祛风,内风要恢复它的阴阳平衡,叫熄风。
热病引起风,风气通于肝,内风,多把它归纳为肝风的范围。肝经热盛,热极动风。本质上来讲,它是与温热病邪,伤耗人体的阴液,阴液缺乏了,使得筋脉不能和柔,本来筋脉应当是既有阳刚又有阴柔,活动自如,失去阴液濡润以后,所以造成热极动风,可以有像手足抽搐,这类动风现象。从证候来看,往往伴有高热,它是温病达到极期阶段,以高热为特点。高热就要热扰心神,造成轻则烦躁,重则神昏,这心神病变。同时刚才我们讲到,热病伤耗阴液以后,造成筋脉失去濡养,手足抽搐,当然这个抽搐程度要根据热盛的程度,以及筋脉失养的程度。严重的可以有角弓反张。舌绛而干,脉弦数。舌绛而干说明伤及阴血了,脉弦数是肝热的特点。
本方证为温热病邪传入厥阴,肝经热盛,热极动风所致。肝经热盛,故高热不退;热扰心神,则烦闷躁扰,甚则神昏;热极动风,且风火相煽,灼伤津液,筋脉失养,以致手足抽搐,发为痉厥。肝热风阳上逆所致的头晕胀痛、手足躁扰等,机理亦同。治宜清热凉肝熄风为主,佐以养阴增液舒筋为法。
方中羚羊角入肝经,凉肝熄风,钩藤清热平肝,熄风镇痉,共为主药。桑叶疏散肝热,菊花平肝熄风,助主药以清热熄风,共为辅药。火旺生风,风火相煽,最易耗伤阴液,故用鲜生地、生白芍、生甘草酸甘化阴,增液缓急;邪热亢盛,每易灼津为痰,故用川贝、竹茹清热化痰;风火相煽,必上薄于心,故又有茯神木平肝熄风,舒筋通络,宁心安神,以上共为佐药。生甘草又能调和诸药,兼以为使。诸药合用,共奏凉肝熄风,增液化痰,舒筋通络之。
加减用药
若热盛者,可加大青叶、板蓝根、夏枯草、草决明等以增强清肝之效。若热邪内闭,神志昏迷者,可配紫雪丹、安宫牛黄丸等清热开窍之剂。若高热不退耗伤津液较甚者,可酌加玄参、天门冬、石斛、阿胶等滋阴增液之品。若神昏痰鸣者,可加天竺黄、竹茹、姜汁,以清热豁痰。抽搐甚者,可加全蝎、蜈蚣、僵蚕、蝉蜕等熄风止痉药。若热邪偏于气分者,可加石膏等以清气热,若热邪偏于营血者,加犀角,牡丹皮以清营凉血等。
禁忌若邪热久羁,耗伤真阴,以致虚风内动者,又非本方所宜。
各家论述
《重订通俗伤寒论》何秀山按:以羚、藤、桑、菊熄风定惊为君;臣以川贝善治风痉,茯神木专平肝风;但火旺生风,风助火势,最易劫伤血液,尤必佐以芍药、甘草、鲜生地酸甘化阴,滋血液以缓肝急;使以竹茹,不过以竹之脉络通人之脉络耳。
《谦斋医学讲稿》:本方原为邪热传入厥阴、神昏抽搦而设,因热极伤阴,风动痰生,心神不安,筋脉拘急。故用羚羊、钩藤、桑叶、菊花凉肝熄风为主,佐以生地、白芍、甘草甘酸化阴,滋液缓急,川贝、竹茹、茯神化痰通络,清心安神。由于肝病中肝热风阳上逆,与此病机一致,故亦常用于肝阳重证,并可酌加石决明等潜镇。
附方
①钩藤饮(《医宗金鉴》),由钩藤、羚羊角、人参、全蝎、天麻、炙甘草构成。功能清热祛风,益气解痉。主治小儿天钓,手足抽搐,牙关紧闭,惊悸壮热,头目仰视及气虚者。
②镇风汤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),由钓藤、青黛、羚羊角、龙胆草、清半夏、生赭石、僵蚕、茯神、薄荷叶、朱砂构成。功能清肝祛风。主治小儿急惊风,其风猝然而得,身极颈痉,四肢搐搦,神昏面热,或痰涎上壅,或目睛上窜,或牙关紧闭,或热汗淋漓。
③熄风宣窍法(《医方嚢秘》),由羚角片、真滁菊、钩藤、明天麻、冬桑叶、蝎尾、橘络、陈胆星、法半夏、白茯芩、鲜石菖蒲根汁、淡竹沥构成。功能宣窍熄风,化痰通络。主治卒中神志不清,痰涎上壅,口眼歪斜,口不能言。
④清热熄风汤(《中医治法与方剂》),由石膏、银花、莲心、连翘、竺黄、大青叶、炒栀子、钩藤、蜈蚣、全蝎、僵蚕、地龙、蝉蜕、菖蒲构成。功能清热解毒,祛风止痉。主治热盛动风,昏迷,抽搐,谵语,舌质绛,脉弦数。
⑤羚羊镇痉汤(《温病刍言》),由羚羊角粉、生石决明、生石青、龙胆草、全蝎、僵蚕、钩藤构成。功能祛风镇痉,清热平肝。主治温病高热不退,热极动风而致四肢痉挛抽搐,颈项强直。
⑥龙胆羚羊角汤(《中医妇科治疗学》),由龙胆草、干地黄、黄芩、羚羊角、茯神、车前子、丹参构成功能清热平肝,熄风养血。主治子痫,偏于风热。未发之前,头痛甚剧,头昏眼花,面色发红,大便秘结,脘腹疼痛,或有呕吐;病发后,神昏抽搐,舌质红,脉弦滑而数。
⑦疏成清热饮(《实用中医小儿科学》),由清水豆卷、桑叶、连翘、炒栀子皮、薄荷、黄芩、僵蚕、钩藤、菊花。组成功能清热镇痉,主治急惊成高热期,壮热,面红唇赤,涕泪俱无,头部剧痛。
医案精选
偏头痛
王某某,女,52岁。年9月初诊。左侧偏头痛近来频繁发作2周,剧痛如裂,恒以手按,痛得稍减,自觉头重足轻、行走不稳。病人偏头痛史已达10年,有家族史,每逢季节更替尤易发作。曾经某院脑CT检查无器质性病变,选用西药疗效不佳。
刻诊:烦躁,胸闷,纳呆,夜不安寐,视物模糊。检查:血压/80mmHg,苔薄白腻、舌有瘀点,脉弦滑。证属肝风挟痰,上扰清窍,经络瘀滞。遂予羚角钩藤汤加减
处方:山羊角18g,钩藤15g(后下),菊花9g,细辛4.5g,全蝎、蜈蚣各1.5g(研粉吞服),川贝母3g(研粉吞服),天麻9g,姜半夏9g,延胡索12g,茯苓12g,生甘草4.5g。服药2周,偏头痛明显减轻,纳香寐安,神志清爽。
二诊:血压/75mmHg,脉细而滑,苔薄白,上方加胆南星9g,生白芍12g。继服2周,头痛消除,其他症状亦明显好转,随访1年未复发。
本方主治热邪传入厥阴,肝经热盛,热极动风之证,故用本方以清热凉肝息风为主,配合增液舒筋。证中因邪热炽盛,故高热不退;热扰心神,则烦闷躁扰,甚则神昏;由于热灼阴伤,热极动风,风火相煽,以致手足抽搐,发为痉厥。所以临床以高热烦躁,手足抽搐,舌绛而干,脉弦数为辨证要点。
病毒性脑炎
张某某,男,27岁,农民,年5月16日入院,家属代述。主诉:四肢无力,沉默寡言10天,神志不清2天。
现病史:病人于4月下旬因劳累及情绪不畅,继之感头痛,无力,但不发热,未受外伤,尚能够坚持工作。5月7日出现频繁呃逆,头痛加重,伴有烦躁,难以入睡,2天后精神极度疲乏,手无握杯之力,呵欠不断,出现嗜睡不语,反应迟钝。进食时,由他人喂给,医院每天肌内注射安乃近1支。至5月12日,吞咽困难,表情较痴呆,医院急诊。2小时后逐渐失语,低热自汗,四肢时有痉挛屈曲,小便亦失禁。5月15日,神志不清,大小便失禁,拟诊“痉病”给予对症治疗,但未见好转。于5月16日晚转我院急诊。
既往史:曾患伤寒(年6月),已治愈。入院检查:T38.7℃,BP/64mmHg。发育营养中等,神志不清,汗较多。全身皮肤未见伤痕、溃疡及出血点。浅表淋巴结未触及。巩膜无黄染,双侧瞳孔等大,角膜反射存在,外耳道、鼻腔无脓性分泌物。牙关紧闭,喉中痰鸣,项强。心律齐,无杂音。两肺呼吸音较粗。肝肋下可触及,质软,边缘光滑,脾未触及。双上肢肌张力增强痉挛屈曲约30°,左手不时震颤;左下肢肌张力高,右侧正常;左股二头肌反射较右侧弱。腹壁反射及提睾反射消失。双侧膝反射存在,双侧克氏征(+),双侧巴氏征(+)。化验检查:白细胞11.6×10/L,中性粒细胞0.83,淋巴细胞0.12,单核细胞0.01。两次脑脊液常规检查及糖、蛋白、氨化物定量基本正常。血沉、抗“0”、血糖、非蛋白氮、电解质、二氧化碳结合力、肝功能等均正常。摄胸片示:肺纹增粗。西医诊断:病毒性脑炎合并肺部感染。入院后经激素、能量合剂、抗感染等治疗9天,神志仍未清醒,不大便已10天,小便自遗,量少色黄,双下肢强直,双侧膝反射亢进,症状无改善。因单纯西药治疗不佳,5月23日改为中药治疗。暂停激素,症状、体征同前,诊脉弦滑,舌质绛红、苔黄厚而糙。
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谓:“诸暴强直,皆属于风”“诸禁鼓栗,如丧神守,皆属于火”。病人郁闷不舒,郁久化火,火极生风,挟痰上升,其脉症属一派风火痰热之象,故治宜平肝息风,豁痰开窍,泻火通腑。仿羚角钩藤汤化裁
处方:羚羊角3g(磨冲服),钩藤60g(后下),菊花、胆南星各12g,石菖蒲、郁金各12g,白芍30g,石斛15g,黄连6g,生大黄15g(后下)。每日1剂,分3次服。
经鼻饲喂药2剂后,呼之能答应,能够伸右手接物,但定向不准,四肢拘急有所减轻,大便日行4~5次,先为黑色干便,后为褐色稀糊便。守上方加丹参12g,浙贝母6g,磁石30g。再服3剂后,能进少许流质,舌苔由燥转润,但出现频发呃逆。拔去胃管,续服上方。
6月3日(共进药11剂):神志转清,能正确回答一些问题,但吐词欠清,呃逆减轻,体温正常。唯情绪激动时有四肢震颤,近事记忆完全消失。仍守上方加桃仁10g,红花3g,龟甲30g,黄菊花6g,再进3剂。此后,舌质转为正常,苔由黄转白,脉弦细,守上方加牡丹皮10g。
6月20日:病情明显好转,吐词亦清楚,并且自己可翻身,左上肢屈曲,能伸90°,近事记忆有所恢复。至6月底能自觉便意,双下肢能正常活动,站立呈后倾体位,坐不稳。
7月23日:上方去羚羊角、牡丹皮,再服1周。此后可逐步扶车行走,左肘关节能伸°。
7月23日:小便能控制,能够坐稳,站立,随意行走。当天的事情能记清楚,左上肢能伸°,舌质淡、苔薄白,脉细缓,饮食睡眠、二便尚可。续服上药,略减剂量。
8月4日:病人自觉牙齿松动,嚼食无力,虑为肾阴不足所致,以知柏地黄汤加减。服药2周后,觉牙齿松动明显好转。查体:颈软,心肺肝脾均正常,生理反射存在,病理反射未引出。复查血常规、非蛋白氮、电解质等皆正常,于8月20日出院。
按语本病分为三个治疗阶段。第一阶段的治疗原则是平肝息风,豁痰开窍,泻火通腑为主,以羚角钩藤汤化裁。方中羚羊角、钩藤、菊花平肝清热,息风镇痉为主药,剂量亦较大;胆南星、石菖蒲、浙贝母、郁金豁痰开窍,通络泄热有助于醒脑;石斛、白芍养阴增液,缓肝舒筋;生大黄、黄连能泻火通腑解毒。第二阶段神志清楚,据“久病必瘀”之理,在原方基础上加桃仁、红花、丹参、牡丹皮以活血化瘀,减轻炎症反应。活血化瘀与清热解毒药同用,既可改善血液循环,又加快炎症产物的清除及毒素的排泄,促进炎症吸收。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引起脑缺氧时,常伴有脑血液循环障碍,故活血化瘀药能改善脑血循环和血氧供应,增强机体对缺氧的耐受性,有促进苏醒作用。龟甲、磁石镇静宁神,养阴生津,清心除烦。诸药剂量,随症加减。第三阶段,病人食欲、二便、睡眠均好,活动自如,但感牙齿松动,嚼食无力。盖齿为骨之余,属于肾。当为肾阴不足之证,故以知柏地黄汤化裁,滋阴泻火以善其后。[黄朝阳.羚角钩藤汤化裁治疗病毒性脑炎1例.南京中医学院学报,,(2):-]。
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中医师指导下使用。如照方抄录服药,后果自负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baobaoyijia.com/mytyzl/12947.html
- 没有推荐文章
- 没有热点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