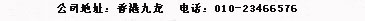普济除疫二线方兼议圣散子方
宋代文人多知医,故有大量文人医著传世,尤以宋末学者选录苏轼与沈括手集方合编之《苏沈良方》著称。书中不乏传世妙方,其中“苏氏圣散子方”历来则毁誉参半。
该方来历在宋人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记载甚详,“子瞻在黄州,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,得仲景意。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,初不见于前世医书,自言得之于异人。凡伤寒,不问证候如何,一以是治之,无不愈。子瞻奇之,为作序。比之孙思邈三建散,虽安常不敢非也,乃附其所著《伤寒论》中,天下信以为然。”
但叶氏尖锐地指出:“疾之毫厘不可差,无甚于伤寒,用药一失其度,则立死者皆是,安有不问证侯而可用者乎?”并记录了“宣和后,此药盛行于京师,太学诸生信之尤笃,杀人无数。今医者悟,始废不用。”可见该方起初应用颇有验,以致于伤寒大家庞氏亦不敢非之,然而到北宋末年,此方一度“惹祸”,渐被时医弃置不用。
因此后世医家多认为该方之收录是苏氏败笔,如明季俞弁《续医说》:“昔坡翁谪居黄州(在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)时,其地濒江多卑湿,而黄之居人所感者,或因中湿而病,或因雨水浸淫而得,故服此药而多效,是以通行于世。”但“方中有附子、良姜、吴茱萸、豆蔻、麻黄、藿香等剂,皆性燥热,反助火邪。”
那么该方是否真的一无是处?实则中医制方各有式法所依,式法不同,则不可同一而论。南宋陈言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一语中的——“此药以治寒疫”,已经将机要道尽。黄州地处湖北,民多中湿而病,该方立义正在于此,诚转阴出阳之良方。观伤寒式法之用在于六经表里,而圣散子方立法与伤寒所用式法不同,故宣和间医家以伤寒法理解应用,可知其无益反害,若更逢温热流行,则鲜有不杀人者,可见中医治学之难,而非方之不效。
沈谦益先生弟子赵阳试解该方之原旨:麻黄、细辛透阴中邪气;独活引猪苓、茯苓、泽泻去肾中郁水,使从膀胱而出;菖蒲通九窍打开道路;高良姜温肝胆之路,从阴转阳以发热,用柴胡、芍药、枳壳开通胆腑,后用防风、藁本散邪透表;白术利腰脐,因胃为肾关,以协调脾肾;甘草引厚朴、藿香、半夏、豆蔻去脾胃中滞留之湿,杏仁开水之上源,黄芩、石膏去肺和脾胃之热。此方专擅治不发热或发热不明显之寒疫,是其妙用!当下武汉疫情同样存在部分患者发热不明显之特点,故该方大可参考,以为普济法之二线方剂。
临证要点:此方为前面普济除疫一线方用药24--36小时后效果不理想时候的二线用药,舌质不红绛者,用圣散子方加味。舌质红绛者,重症发热病人可用普济除疫一线方,生石膏3~4倍用量,酌加寒水石常量。圣散子方加味
草豆蔻(炮)40g、猪苓、石菖蒲、高良姜、独活、麻黄、厚朴、藁本、芍药、枳壳、柴胡、泽泻、白术、细辛、防风、藿香、姜半夏各20g、制甘草40g、枯芩20g、茯苓20g、杏仁20g、生石膏60g。
为粗粉,每服15克,水毫升(约三纸杯),煮取毫升(约二纸杯),去滓热服。余滓两服合为一服,重煎,空心服。
附:普济除疫一线方
藿香、厚朴、杏仁、茯苓、陈皮、神曲、麦芽、甘草、大腹皮、紫苏、半夏、白芷、桔梗各等份。不发热加草果,发热加石膏(倍量)黄芩。上为粗末,每用15克,姜三片、枣2枚,水煎服。或者用科学中药颗粒剂,按浓缩比用药。频服,以知为度。小儿酌减。
(拓展阅读:《献出中医除疫方,中医智慧护佑中华儿女!》)
讲者简介张驰,男,年出生,籍贯吉林省长春市,民革党员。长春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教师,民革党吉林省直中医药支部支委,颐仁青年中医会理事,世界中医联合会青年中医培养工作委员会理事,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术传承与创新联盟理事。
年就读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,同年师承昆仑医宗沈谦益先生,传承孙真人一脉四部九家学术。研究生攻读长春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王军教授硕士,参研《伤寒论》教法。年留校任教。
著有《新刊四海同春疏注》(学苑出版社,),《中医五运六气全书》(世界出版集团,),《伤寒论钱塘章句疏要》(学苑出版社,)。主持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:“伤寒气化学派理论传承与研究”(结题,项目编号:-wt2)
自年初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传统诊疗中心出诊,临床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baobaoyijia.com/jxmyty/12761.html
- 没有推荐文章
- 没有热点文章